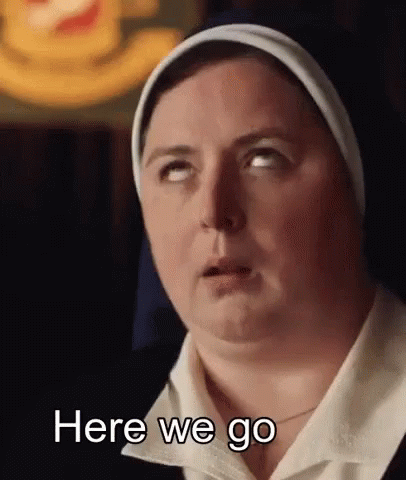
比较文学博士在读,口译员。
方块字出逃记
早上7点,我像往常一样被闹钟闹醒,迷迷糊糊地开始刷手机醒神。
今天的手机界面看起来有点不一样,莫名多出来许多空白处,原本密密麻麻的图标之间隔出几道宽宽的缺口。仔细一看,原来每个图标下方的文字全都消失了,仅留下时钟的数字孤零零地悬浮在屏幕中央。手机又发神经了。我抓着它往左手手心拍了几下,就像小时候我妈总爱在电视飘雪花时拍两下一样。拍一拍就能好,这是家电修理的玄学,徒劳却必要的心理安慰。文字没有因此回到屏幕上,可能要送去检修。我一边想着,一边点开了社交软件的图标。
眼前的图像彻底把我从睡意中震醒。整个屏幕像被入室抢劫过的房屋,有些地方空空如也,有些地方一片狼藉。短小的线条雪花般焦躁地逃窜,过一会儿就消失不见了,也不知道它们都去了哪儿。我盯着看了好一阵子,才发觉那是方块字的笔划。点、横、竖、撇、捺。他们组成一条松散却迅疾的队伍,乱中有序,让我想到穿越茫茫沙漠的搬家蚁群。
头像右方的名字全部成了一串数字,应该是每个账号在后台的代码。发言框里只剩大片空白,偶有几串歪斜扭曲的乱码四散在各处,像劫匪一脚踢进角落的破拖鞋,又像长久在暗处堆积的蜘蛛网。没有了方块字,零星的外域字符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如同一幢拆迁建筑的残垣。甚至连残垣都称不上,那不过是失去了凭据的砖缝里疲软挣扎的杂草。但我依旧像在沙漠中发现了绿洲,迫不及待想分辨出这些最后能产生出明确意义的符号。
NMSL。NM$L。
N
M
S
L
N
M
$
L
$$$$$$$$$$$$$$$$$$$$$$$$$$$$$$$$$$$$$$$$$$$$$$$$$$$$$$$$$$
我如获至宝,双手捧着扁平的机器,忍不住要亲吻这仅剩的我能看懂的四个字母。它们瞬间将我从意义的荒芜里拯救出来。原来还不至于沦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我从未感到如此欣慰和安然,不禁振臂高呼。NMSL!NMSL!NMSL!呼满意了,又重新拾起手机,想要好好端详这四个字母的形貌,好让自己从这貌似阅读的端详里获得更丰富的踏实感和更踏实的丰富感。我把手机举到靠近鼻尖的位置,恨不得整个人都埋进去。近距离的端详下,字母的线条好像起了什么奇怪的变化,诡异地蠕动着,有时抽搐起来,又结成一个黏腻的线团,在身后留下一串湿乎乎的痕迹。它们好像某种能进行无丝分裂的虫子,躯体在某个节点断裂开来,一下便分成了两道一模一样的线条,只是两者中间横着若干细细的未被切断的细丝,形如哥斯拉张嘴时上下唇中间藕断丝连的黏液。一股灼热的酸从胃部涌上喉咙,我被这突如其来的灼烧感刺激得热泪盈眶,一时竟分不清是被感动的还是被恶心的。我跑去卫生间呕吐,吐着吐着,愈发空虚的胃里又似乎被某种羞愧感填满了。有个声音在脑海里训斥自己刚才振臂高呼的傻X样,我怒着劲儿想听清那训斥的内容,却只听到尖锐的笑声和四个字母:NMSL。
原来赛博世界里是有风的。风把杂草在平日里吹出长牙舞爪的形状,把种子播散到楼宇的缝隙里。NMSL。NMSL。NMSL。此刻它们成了赛博广场的霸主,即便东倒西歪、抽搐狰狞,却依旧发出自鸣得意的刺耳合唱。
我感觉自己应该对这一连串的异状发问,但又并不感到十分必要。甚至连这是否是异状,我也不甚清楚了。有时我对身边的事情感到奇怪,但看着人们全都神色如常,便怀疑我觉察出的怪异只是一场幻觉。我惊讶,却隐隐有些早有预料的平静。困惑,却又有种了然于胸的明晰。这感觉好复杂,仿佛是看见了什么早就隐隐然感到会发生的事情,只是没想到会发生在这一刻。那些长期包裹着我的混沌,那些来由不清去向不明的疑问,在此时居然裂开了一道尘埃落定的口子。我呆看着手机,只觉得思绪和身体都异常迟滞,抬头、张嘴、迈步,全都被无数根细细的线有意图地钳制住,惟有大拇指滑动屏幕的速度不降反升,让荧荧屏幕滚动成一片语焉不详的模糊。我害怕指尖的摩擦会让手机就这么着起火来。眼看着方块字逃窜,我感觉自己体内的水分在迅速蒸发,很快就要变成一具失去血肉的人干。连这蒸发的感觉都有种陌生的亲切,也许我已经被晾晒很久了。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但日子总得过下去。我已经在这场意外的混乱里浪费了半个多小时,再这么下去要迟到了。老板是不会听你为迟到找理由的,何况早上的见闻说给他听,他只会觉得我是神经病。可能只是压力太大了,晚上回家要好好泡个美容澡。我飞快洗漱好,囫囵啃了两块饼干便出了门。但门外的景象却比我在手机里看到的更为荒诞和疯狂。所有物体上的方块字——指示灯旁边的路牌、商铺的霓虹字体彩灯、甚至路人手里矿泉水瓶上的标签——都在挣扎着向外逃逸。他们残缺的身体如水母般在空中悬浮。这逃逸的过程远比屏幕上的暴力。有一个不锈钢“大”字招牌,大概是因为身躯的沉重困顿了它奔跑的速度,那一横于是弯折了双手,先扯下“人”的两条腿,再把一横上的头掰了下来。肢解自己的过程中,有一小块铁皮落下,断肢的截口漏出弯曲的钢架子。于是那一撇、一捺、原本属于一撇的短竖和已经弯折了的横,就这样齐齐向空中飘去了。环顾四周,这样拆分自己身体的字不在少数。他们不带半点犹豫,将自己撕烂、碾碎、砍断,直到足够轻,轻到能毫不费力地成为云的一部分。
我看得目瞪口呆,好像那“大”字掰的是我的头,在后脖颈处留下断裂的痛感。我看向与我一样目瞪口呆的路人,想开口询问些什么,但话到嘴边却轻巧地滑落下来,我发不出声音,只能看着无数笔划随着嘴唇的开合掉下,然后像那个“大”字一样,直直追着天边而去。
我想我是这时才真正从梦中醒来。这是一场事先计划的逃离。方块字逃走了。我瘫坐在路边,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下来。不是因为悲伤,纯粹是因为受到了刺激。可在这时候最先跳进脑海里的还是我的饭碗。我好像忽然才想起来自己是一名图书编辑,字都不见了,估计我们都要失业了。怎么办呢?我仅剩这点给字画圈加批注的技能,别无所长,我还能如何养活自己?但世界已经成了这副没人能看明白的样子,担心失业又有什么意义呢?别说意义,意义的载体和意义本身,都无法在这片土地上存活。我拿出手机,往常的这个时候工作群里应该已经消息一浪接一浪,同事们排着队给老板无聊的晨间鸡汤发送大拇指。但今天一片死寂,字全都逃跑了,老板的晨间鸡汤失去了宿主,自然也没有比大拇指的必要。我索性换了个舒服的坐姿,心安理得地欣赏起这好莱坞大片也拍不出来的奇观,一边试图给这奇观追溯一个源头。
说来还是有些惭愧。我一个天天跟方块字打交道的人,居然没有比其他人更早发现他们的焦急与恐惧,只能跟无数平常路人一样为此刻震惊。我自诩热爱文字,但我可曾关切过文字的爱恨情仇呢?我们视方块字为工具和容器,只顾着把自己的愤懑往里倾倒、举起大字扔向骂战中的另一方,却不视方块字为与我们同等的、具有肉身与性灵的存在。他们的悲伤想必是持续很久很久了,即便肢解自己、分崩离析也要逃离,他们该有多绝望呢。方块字被戕害的确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我之前只把这当成是对我的戕害,是对所谓热爱知识与自由的灵魂的戕害,却不曾想过铁锤是直接砸到了方块字的身上,而我们不曾帮一笔一划分担丝毫疼痛。我们只是兴致勃勃地围观这场缓慢的屠杀,以此为顾影自怜的借口。
我忘记最早被枪决的方块字是哪个了。但反正是有那么个字,有无数个命运与她类似的字。先是不允许在报纸上出现,然后是不允许在书本上出现,最后是不允许在任何地方出现。现在所有人都像我一样,忘记了那是个什么字,忘记了其他的许许多多个字。他们也必然曾挣扎着想要努力活下来。前几年的冬春之交吧,有一篇文章里的方块字遭到集体处决。为躲避刽子手,他们乔装打扮,扮成甲骨文,扮成火星文,扮成洋文,扮成代码海洋里的一朵浪。最后他们勉强活了下来,但只能以乔装的面貌示人。它们不再能被人读懂,出其不意的乔装只被世人当作一场大型的行为艺术,他们还是死了。
我又掏出手机,点进平时常用的新闻直播软件,我想看看新闻会如何播报这一切。主播依旧努力尽职地念着稿子,但就像我一样,无数笔划从她的嘴里落下,有些飘出了直播间,有些堆叠在脚边,有些在向上逃逸的过程中被天花板阻隔。一些笔划黏到了她因紧张而冒汗的脸上,像擦过汗后面巾纸留下的纸屑。她用手背轻轻拂拭,力图保持优雅,但笔划却怎么也擦不下来。她终究是不耐烦了,想用手掌大力一抹,却不知怎的扇了自己一个大耳刮子。主播是电视台的元老级人物,一直以正统的端庄形象示人,但现在她的脸成了绛紫色,不知是被自己那一巴掌扇的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密匝匝的白色笔划固执地不肯离开她的面颊,让她看上去像一个霜打的茄子。她看上去那么紫,紫得像快要爆炸了,我真怕下一秒她的脸就会炸出葡萄汁儿,越过屏幕溅到我脸上。我饶有兴致地看着她在爆炸边缘徘徊了几分钟。她似乎努力地在控制自己,想要把蓄势待发的葡萄汁儿憋回去。但就在我觉得她要爆炸的那一瞬间,主播忽然双手握拳,身体前倾,脖子伸得老长——NMSL!!!!!她大喊一声,我的手机小小地震颤了一下,差点掉到地上。接着她露出了如释重负、久旱逢甘霖的表情,举起双臂接连高呼NMSL,大概我早些时候看起来也是这样子。这可真是太糟糕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傻X的画面,但更让我受打击的是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也是这傻X的一部分。
街上的人陷落在狂热里,并对这疯癫甘之如饴。人们说不出别的话,只能喊NMSL。但大家都搞不清楚对方喊这句话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便都觉得是在骂自己和自己妈。稍微斯文点的隔着一丈远的距离,红着眼互喊NMSL,他们全都像女主播一样,脖子恨不得要抻得能把脸怼到别人的鼻尖,脚却像打了钉子般一动不动。脾气炸的直接就冲上去对打了,一边挥拳,一边还要喊着NMSL起个范儿。更搞笑的是有看上去想劝架的人,双手伸开拦在两个人中间。他的两条眉毛向下撇着,忧心忡忡的样子,但嘴里却仍在念念有词——NMSL。于是两个原本要对打的人又被这个劝架的激怒了,同仇敌忾地想要一起揍他。
也有与之完全相反的另一群人,仿佛找到了失散多年的革命同志,排成整齐的方队高唱NMSL。他们个个两眼放光,似乎准备好了要为伟大事业献身。唱歌的时候,他们把拳头举过头顶,随着节奏一下一下地挥舞。
此时已是下午,没想到我已在街道的角落里坐了大半天。我害怕被人围殴,也不想加入合唱的方队,便猫着腰一路小跑回了家。方块字已逃了大半,但人们似乎并不为此感到奇怪或悲伤,就像以往的任何一次一样。有商家迅速定做了NMSL的铝合金招牌,已在准备安装。很快,这条街上就会被NMSL占领。工作群恢复了热闹,先是老板发了一长串NMSL,然后大家整齐地发送大拇指。这片土地有抵抗异状的强大能力,人们总能第一时间恢复到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然后把新的规则当作从来就有的规则。我忽然想起了什么,于是把手机系统切换成了外域语言模式。文字又重新回到了屏幕上,只是不再是方块字。我有些许安慰地想到,还好,我们不是一无所有。
我搭了梯子去看外域的网站,因为只能说出NMSL,所有的外事活动都成了外交事故。大批海外侨民因此受到歧视。一个外域主播流畅播报着这里发生的一切,用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字。我有些羡慕,又疲惫得差点要忘却羡慕了。这一天太过漫长,太过疯狂,也许它依旧只是我做的一场梦。睡一觉,第二天就会一切如常。
喧闹终于随着暮色的降临而退潮,我趴在窗口往天空看,竟看到满天星斗。城市常年被雾霾占领的半空清澈透亮,仿佛经过一场宇宙的洗礼。他们终究是比云厚实沉重太多的存在。他们去到了远方,化身无数个星球,在迢遥的星际发出光亮。我有些失神,不知道是是我们赶走了方块字,还是方块字抛弃了我们。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