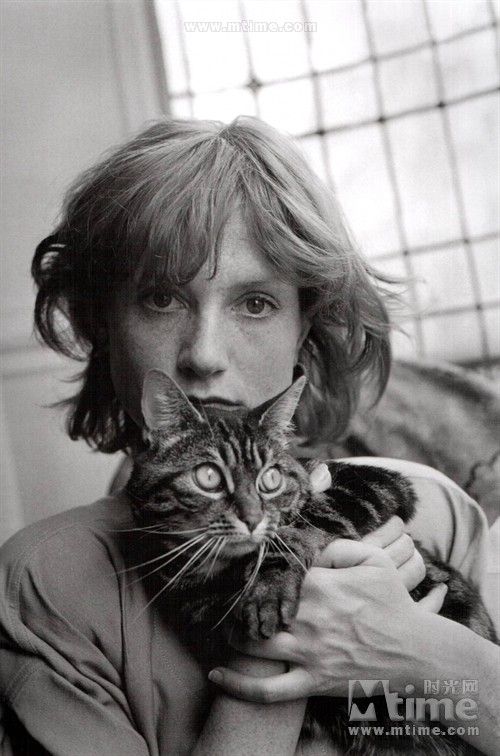
在劇場裏摸爬滾打,在文字裏安生立命。
房思琪们开口说话,炸毁“反转”和“仙人跳”

林奕含离开三年了,4月27日是她的忌日。身在天国的她若得知最近的“N号房”事件,和“鲍毓明性侵未成年养女”一案,不知道是不是要难过地哭出声来。她生前在访谈里说,李国华们不会死,也不会死,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生。现实确实如她所说,在你阅读这篇文章的间隙里,每3分钟就有一个女人被打,每5分钟就有一个女人被强奸,每10分钟就会有一个小女孩被性骚扰/性侵。女性的一生,就是一部暴力史。
林奕含在书写《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过程中非常痛苦,因为她无法通过这本书来救赎“生活在痛苦与暴乱中的自己”,更不能救赎任何人。这让善良的她认为自己是个废物。即便当时她的状态非常不好,她还是说出了房思琪们的故事。林奕含所做的努力不止于此,甚至可以说,林奕含用自己的生命,带动了台湾的Me Too运动。
时光荏苒,世界没有变好,但依然还有很多人在为明天努力。林奕含们在努力,伊纹们在努力,房思琪们也在努力。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女孩被诱奸的故事,而是女性自打出生开始,被囚禁的一生。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用了大量的细节描写,来表述女性被闭锁于窥镜/封闭之中。在第一章“乐园”之中,写怡婷在厕所里照镜子——“大厅厕所的镜沿是金色的巴洛克式雕花,她的身高,在镜子里,正好是一幅巴洛克时期的半身画像”。怡婷从镜像之中,得出“扁平的五官上洒满了雀斑,脸几乎是正方形的”,自己长得不好看的结论。怡婷的结论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吗?还是说,是来自于男性的凝视和男性审美的建构?每一个年轻女孩在学习成为一位美丽的客体过程中,也就是在被迫接受的教育里,一步步放弃自己的“主体”过程。女孩学会了对她自己的身体产生焦虑感——或许甚至还有厌恶感。她对围绕在她周围的那些真实的和象征意义上的窥镜入迷地凝视着,渴望自己的脸蛋更“漂亮”一些,自己的身材更“苗条”一些。
再来看李国华第一次在电梯里见到思琪的场景描写,“金色的电梯门一开,就像一幅新裱好框的图画”,暗示了思琪还未来得及长大的人生被困在了李国华的画框里。李国华又从电梯的镜子里,看到镜子里的思琪“脸颊是明黄色,像他搜集的龙袍,只有帝王可以用的颜色,天生贵重的颜色”。李国华的爱好除了喜欢强奸小女孩之外,还特别喜欢收集龙袍。他把自己当成了皇帝,把补习班当成了他的天下,把补习班的女生当成了他后宫选妃的地方。接下来,李国华开始感叹思琪“还不知道美的毁灭性”(美并没有毁灭性,美也没有错,有错和有毁灭性的是以强奸小女孩为乐的李国华们),看到她学号下隐约的粉红色胸罩边沿,连没有蕾丝花和钢圈的细节都观察到了,这在李国华的眼里是“一件无知青少女胸罩”,甚而觉得白袜在她的白脚上都显得白得庸俗了。这一段描写,就是李国华从头到脚地将思琪审视了一番。这种男性的凝视,令有良心的读者感到极度不适。作者的目的也达到了——感到不舒服,是每一个女性的日常之一。现实生活中,少有男性会受到李国华这种凝视的洗礼。
当李国华再一次在电梯里碰到思琪和怡婷的时候,他从思琪的脸上看到了楼上女主人伊纹的脸——“一张初生小羊的脸”,然后说自己不碰有钱人家的小孩,因为麻烦。李国华选择思琪并不仅仅是因为她从小的淑女教育和自尊心,而是他发现社会对性的禁忌,“强暴一个女生,全世界都觉得是她自己的错,连她都觉得是自己的错”。更多的原因,是思琪和饼干、晓琦一样,是“一个个小女生在学会走稳之前”,被李国华“逼着跑起来的犊羊”。小羊,性情温顺,在被剪羊毛的人的手下无声无息,在被宰杀时保持沉默。她们从未见过披着教师(艺术)皮的狼,她们是被李国华吞噬的小红帽。李国华的判断,基于他丰富的狩猎经验。他有和补习班的老师们去红灯区集体狩猎的经验,又有着丰富的个人狩猎经验。他单独行动前,必定有缜密的狩猎计划:勘探地形(找隐蔽安全的小旅馆,买了专门的公寓),怎么设置陷阱,让小羊羔们(小红帽们)沦为他的猎物。
前面说到思琪和伊纹一样都有着“犊羊的脸”,作者也在书中一再强调这点。那么,有钱人家的儿子——钱一维选择跟伊纹结婚,难道没有像李国华那样看到伊纹这只“沉默的羔羊”吗?毕竟,他四十几岁才结婚,有着丰富的家暴历史,“已经打跑了好几个女朋友”。他希望快一点和伊纹结婚,真的是出于“爱”吗?
如果说怡婷是思琪的另一个分身,是性侵害的幸存者。那么,伊纹——对于她们来讲,是她们的未来。伊纹在书中,更接近母亲的形象,同时也是教师的形象。伊纹在思琪、怡婷来她家时,会给她们备好咸点甜点和果汁。她有系统地带她们阅读、看电影,在物质和精神上滋养着她们。李国华的出现,取代了伊纹的位置,打断了思琪“文学的思想、对性的想象、对爱情的想象”等一切的想象。
假如说思琪向伊纹求救,伊纹能救得出思琪吗?我们来看看伊纹——出生名门,二十几岁的年纪,休学结婚。她的生活,从一个公共空间、开放的空间,渐渐退隐到私人空间、局限于家庭范围之内的生活。伊纹与钱一维结婚后的家,“有整整一面墙,隔层做得很深,书推到最底层”。书的前面是钱一维父亲(老钱先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颜色各异的琉璃茶壶(一个喜欢收集琉璃茶壶的李国华?),这些艺术品挡住了伊纹从娘家带来的纪德全集。“《窄门》《梵蒂冈地窖》,种种,只剩下头一个字高出琉璃壶,横行地看过去,就变成:窄,梵,田,安,人,伪,杜,日”。最后,作者用了很直白的文字来暗示了伊纹的人生——“很有一种躲藏的意味,也有一种呼救的感觉”。一个自顾不暇的伊纹,哪里分得出力量来救援思琪?如果说思琪的分身——怡婷因为相貌平庸躲过了李国华的“狩猎”,那么,她们能躲过婚姻这口新娘之井吗?可以说,伊纹的人生,对思琪她们来说,是她们人生未来的某中暗示:学业/事业的中断、家暴、流产等等。
老钱先生并未在自己的家中出场过。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为自己的儿子挣得的家业,有钱的程度,是“即使在这栋大楼里也有钱,是台湾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对于儿子家暴一事,邻居说“老钱只要公司没事就好”。这句话,等于说在老钱眼里,伊纹的命没他家公司重要。老钱先生这一父权形象的在场方式,是通过老钱太太发出声音和思想的。伊纹每次想要从书墙里拿书,得经受一次老钱太太的精致苦刑,“每一次把手擦拭干净,小心翼翼地拿下沉重的艺术品,小心拖鞋小心地毯,小心手汗小心指纹”。伊纹的小心换来得是,从来没有一次打碎过老钱先生的琉璃壶。这也似乎暗喻着,伊纹无力反抗父权的压迫。对于伊纹爱看书,老钱太太也是要“骂”的。因为在老钱太太看来,伊纹的“肚子是拿来生孩子的,不是拿来装书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老钱太太认为女人只有“传宗接代”的生育功能,女人的肚子只能“拿来生孩子”的意思是,女人的肚子万万不可生出一首诗,一本书,一部电影来。除此之外,老钱太太对伊纹的饮食也有一套标准,总是叫伊纹少吃“蛋糕”一类的垃圾食品。如果说伊纹是被困在婚姻里的囚徒,那么,“媳妇熬成婆”的老钱太太,顶多从囚徒升级为看守。看守以为自己拥有了囚徒没有的权利,岂不知,囚徒和看守是同在一条锁链之上。
像老钱太太这样把父权制度内化的女性,不止她一人。像补习班的班主任蔡良,亲手将一个个女生送到李国华的床上。还有宁愿自家穷死,也不愿把女儿嫁到钱家的张太太,却把伊纹介绍给钱一维。补习班的老师们,思琪她们所居住的那栋富丽堂皇大楼的所有人,他们都是共谋者。施诸女性的性暴力是整个强暴文化的阴谋,它用以宣称“女人是男人的性禁脔”,而它的作用则在于将女人关入、令女人遁入“内”与“性”的领域,以便男人和父权社会可以将女人用作工具。它所牵动的机制都深入了每个男人、女人的个人生活。没有哪个男人或女人是“清白”的。
伊纹送给思琪和怡婷的十八岁生日礼物——一双异常精致的鸟笼坠子,“鸟笼里有青鸟站在秋千上,鸟笼有清真寺穹顶,鸟的身体是水汪汪的搪瓷,眼睛是日出般的黄钻,鸟爪细细刻上了纹路和指甲,鸟笼的门是开着的”。青鸟或许可以从开着门的鸟笼里飞出来,可在外面等待青鸟的是什么,是老鹰的利爪,是猎人的枪鸣,还是广阔的天空任翱翔?
思琪内心深处的羔羊,不停地发出尖叫声,因为反抗权威,她疯了。思琪的发疯,正是一种逃离。她的肉体无法在父权制度中逃离,她只得杀死自己的肉体,让自己的灵魂飞走,飞到一处避难所。作为女性的我们在父权统治的社会中无处可逃,无家可归——我们无名,我们无处栖身,我们没有确定的地位——我们是谁谁谁的女儿,谁谁谁的学生,谁谁谁的妻子,谁谁谁的妈妈,谁谁谁的演员,谁谁谁的缪斯,谁谁谁背后的女人.......
思琪用她的日记告诉了怡婷和伊纹真相,用书写的方式找回了她的“主体”。林奕含也是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女性并且面向女性的写作,通过挑战由阳具统治的言论和男性文本,确立了自己不是沉默的地位。她在访谈中,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讲真话,表白自己的内心,表达自己的思想。她铭刻自己所说的话。她在访谈里的讲话,她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从不是笼统的叙事、单一的愤怒、一味的控诉:她将自己的经历写进历史。
现在,我们要开口说话,用女性的文本来炸毁“反转”,用女性的文本来炸碎“仙人跳”。为了粉碎一切,开口说话。
(原文首发公众号“回响编辑部”/2020.4.27)
喜欢我的文章吗?
别忘了给点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
发布评论…